問題意識──關於「藝術家教育」的兩種場景
轉眼間,離開熟悉的藝術大學系統也已經滿五年,雖然我的專職工作都還是在一般意義下的「美術學系」,主要教學內容也與藝評和當代藝術脫不了關係,但我也確實能夠發現其中不算小的差異。如果說在進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前所謂的「藝術教育」主要是「藝術『家』教育」這個說來仍困難重重的問題,到了目前的非藝術大學系統時,這個問題則由一種更像是「推廣」當代藝術的藝術教育問題所取代。雖然我必須說,兩者間的差距僅僅是程度上的,然而,這裡的「程度」涉及的仍然是一種比較系統──而在台灣社會的教育慣習中,「程度」這個詞當然有評價意味──也因此,在適應這種比較所為何來的過程中,我也不得不對於原本較熟悉的「藝術『家』教育」產生了些許懷疑,例如像這樣的問題就很難回答:一個程度上更適合成為當代藝術藝術家的年輕人這種評價究竟從何而來?
兩種場景
首先,這種評價與纏繞著人文學科數十年之久的概念「問題意識」有關。我試著用正面的方式表達,先想像下面兩種場景:在我們面前有一位深具創作潛力的年輕藝術家,他談到他的創作與如何看待過去有關,所以一個適當的問題意識是他知道何以用「田野調查」來描述其創作前期的探索會比「歷史研究」來得更貼近,他能夠清楚表達個人記憶與宏觀歷史間若有似無的關聯,又因為他多採用錄像裝置的展呈形式,對於他帶到展場的那些影像以外的物件,他不僅熟諳這些物件與影像間那不只是互文的辨證關係,也很能說明任何既定影像分類方式都有所例外,因為他自己的作品不僅兼具紀錄片特質,同時又摻雜大量旁白,有點像是近幾年流行的論文電影(essay film),這些旁白剛好用到一些方言,所以他總是記得為影片上英文字幕,總之他還在尋找適當詞彙來陳述他的媒介形式,他幾次提到紀.德伯(Guy Debord)的「異軌」(détournement)還有許多像是「人類世」我不見得真的了解也只能點頭稱是的詞彙。

第二個場景比較沒有那麼燒腦,有話題打不太開的窘境,卻也有很強的後勁:眼前的藝術家同樣年輕,其作品隱含了某些基進的性別議題,但與其說我們是在聽他的作品論述,其實他更多地在描述自己的故事;他的「論述」圍繞著個人或許因為青春而處處刺痛的生命經驗──如果是在我們這群師長的同理心開到最大的條件下,這種表述方式會喚醒一些共鳴,但多數情況是我們在聽聞刺痛青春的當下腦中已經轉換出諸多議題選項,而他接下來並沒有提到他應該略知一二的關鍵字,話題就很容易切換到另一個跟表現形式有關的頻道。毫無意外地,他對於自己之所以透過版畫進行創作的表述還是很個人,儘管其技術早已趨近完美的作品確實充滿潛力,但我們這段對話要不以彼此的生命經驗進行直球對決,要不他就會在師長們補充的爆量當代藝術資訊中感到迷茫:「老師說的問題意識是什麼東西?」回家後他還是決定用自己的習慣來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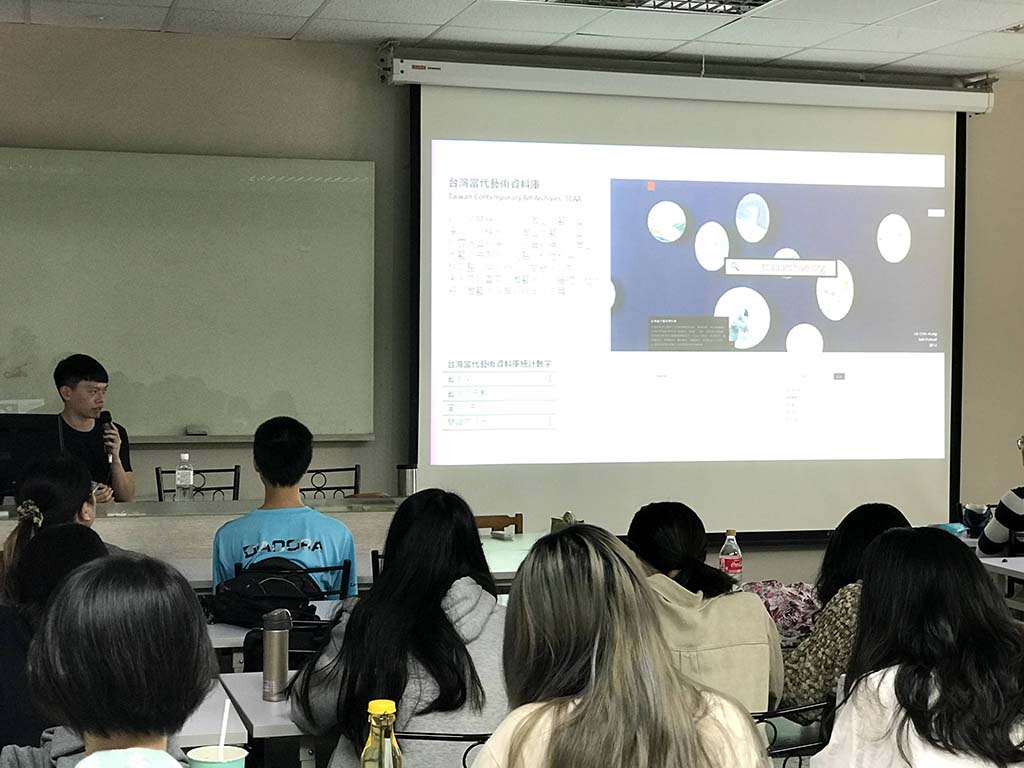
程度與翻譯
之所以說藝大與非藝大之間的差距是程度上的,其實正是因為第一個場景雖然符合我們對於藝大系統的想像,但第二個場景其實也會出現在藝大系統中(反之亦然,只是比例不同),而且,第一個場景中那些高深異常的詞彙也會因為不同的藝大系統出現不同的分配比重。然而,在這兩種場景中,確實存在著很明顯的語言使用差異,前者出現了更多由理論概念所包圍的「議題」,後者則充斥著各種「生活」描述,但在議題與生活間的差距卻不能說是程度上的問題。事實上,就我的教學經驗來說,這兩個場景像是發生在完全不同語言環境中,我置身在第二個場景時,教學活動常意味著對第一個場景進行翻譯,不過第一個場景中的學生通常不太願意描述自己的生活。
當然,第一個場景看來更有利於所謂的「藝術『家』教育」,當我們遇到這種一點就通、甚至資訊量遠大過於老師的學生時,老師需要進行的工作更像是心理諮商,能提供的建議多半是藉由相對豐富的經驗來強化年輕藝術家的信心,或是藉著展示更為周延的思辨過程進行某種「糾錯」,如果老師身上也有一點資源連結,學院中就會出現若干確實是重點栽培的潛力新星。
而第二個場景,要考慮的問題則相對單純,也許藝術家仍然是無法「教」的,但當光是翻譯第一個場景就足以構成一部相當鮮活的「當代藝術知識─系譜」時,所謂的教學目標就會變成,藉著闡述該系譜,讓學生從個人「動機」轉換為關聯於脈絡的「問題意識」;至於要讓他們完成所謂藝術家專業的準備當然遠比前者來得更多,不過也是在第二個場景中,偶然出現的直球對決卻常讓我思索再三──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本來應該是一種主體性進程的「藝術家教育」問題忽然成為一種專業教育?而當老師不再需要對即將踏入當代藝術競技場的年輕人提供前途發展的諮商服務時,我好像忽然明白了這種專業與創傷之間恆常的關聯。(全文閱讀556期藝術家雜誌)
【九月專輯│台灣藝術教育的場景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