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土、他鄉、第三種文化,以聲音與物質文本解讀身世符碼
墨夫.艾斯賓納談例外群體與流動的身分建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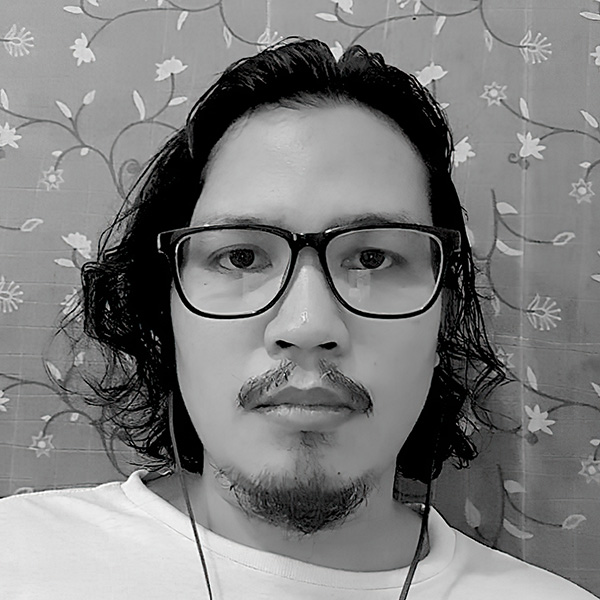
第9屆亞洲雙年展策展人之一墨夫.艾斯賓納
問:你長期關注的聲音與文化研究,如何扣連到近年國際策展中非常關注的全球南方、多元族裔等議題?你又是如何將這些思考融入本次亞雙展的策畫及藝術家名單的選擇中呢?
答:在建構現代意義的「國家」、試圖塑造一個現代意義的國族身分時,人們時常因此失去了其他身分認同。我的父母是移工,而作為移工的後代,我成長的文化彷彿是一種與母文化分離、又與所在地主流文化不同的第三種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總是與其他少數在一起,我特別能感受到,總是有一些身分認同,是例外於主流國族敘事狀態的。在菲律賓還有一個問題,是菲律賓有超過180種語言,我的父母甚至不共享同個母語,而是用英語或菲律賓語(Filipino,菲律賓的通用語)溝通。對我來說,語言一直是文化研究中很有趣、且具啟發性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全球南方」作為一種方法論尤為重要,我的研究也專注於那些不被國族框架、大敘事涵蓋的例外群體與文化。
這次參與亞洲藝術雙年展,我想,召集人方彥翔最初應是希望我能邀請一些東南亞藝術家參展,但我更感興趣的是西伯利亞地區的藝術家,像是來自布里亞特共和國的娜塔莉亞.帕帕耶娃(Natalia Papaeva),她的創作根植於她的布里亞特—蒙古文化背景。彥翔聯絡我時,我正在尼泊爾,我對泛喜馬拉雅地區也非常感興趣。我認為應有一種更開闊的視角去看待泛喜馬拉雅地區的文化。泛喜瑪拉雅地區聯繫著北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的東北方、緬甸、四川等地,在這些地區,人們所共享的其中一個元素竟然是花椒!在尼泊爾的美食中是能見到花椒的。這些看似微小的元素卻揭示了文化的流動與連結。
總之,我為這次亞雙展邀請的藝術家多半都來自少數群體,屬於國族大敘事規則外的例外。像是陶.雷伊.高佛(Tao Leigh Goffe)具有非裔英國人及牙買加華裔的背景,她在倫敦、紐約生活,致力探尋著屬於自己個人的歷史軌跡。還有尼泊爾藝術家伊特曼.古隆(Hit Man Gurung),尼泊爾和英國有著複雜的歷史關係,而在尼泊爾內戰之後,尼泊爾也如菲律賓、印尼,成為勞動力大量外移的國度。這些遷徙與變化,可從食物、織品與圖騰、語言等事物察覺,自然也包括音樂。我從事的聲音研究正是在探討這些地方不同的連結。聲音不只是物理現象,它還承載著歷史、社群與交流的其他種想像方式,體現了超越「國家」的文化格局。
【二月專輯│The Art of Gathering和合與共,當代策展的思辨與實踐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