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羅斯 碉堡裡的收藏家
歷經戰禍的碉堡,如今成為一座私人美術館。乍聽之下或許荒謬,但仔細深思,一個蒐羅、呈現於納粹時代防空洞裡的當代藝術收藏,這樣的天開奇想其實相當合理,畢竟沒有任何一種表達、詮釋人性的載體,比藝術更值得被安然地保存下來。這就是柏林的獨特之處,它時時提醒著人們,歷史雖然不能、也不應該被遺忘,但它可以經由創造性的參與,而持續擴寫與時代並進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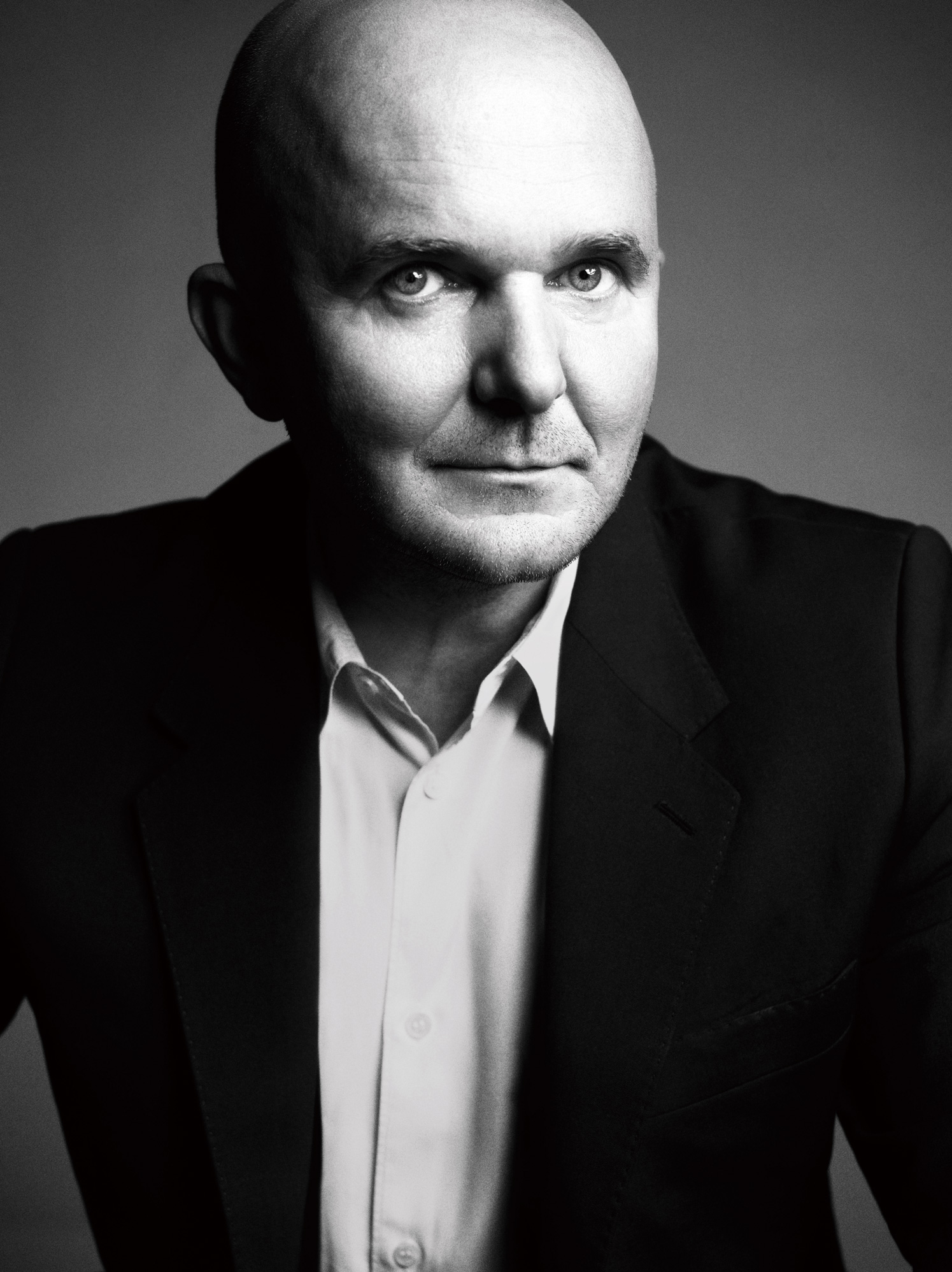
克里斯欽.柏羅斯(Photo: Magnus Reed)
由德國廣告公司創始人與Distanz出版社發行人克里斯欽.柏羅斯(Christian Boros)與妻子凱倫(Karen Boros),以數十年時光建立起來的藝術收藏系統,自2008年起入駐柏林米特區心臟地帶的一座18公尺高、當地人稱「混凝土巨獸」的碉堡收藏館。目前正進行的是「柏羅斯收藏/柏林碉堡三號」(Christian Boros)展覽,展出時程如同前兩檔收藏展,自2017年向大眾開放至2021年。

柏羅斯收藏館外觀(Photo: NOSHE)
為何以四年為期,展出每檔精心規畫的收藏展?柏羅斯表示:「即使我擁有了這些藝術品,我也無法預期何時我有機會再度看到它。由於我所收藏的多數是大型裝置,難有展示的機會,況且每一場收藏展都是促成不同藝術家觀點相互對話的場域,因此我以四年作為展覽檔期的規畫時程。每當構思展覽主題意識時,我首先考慮的是:『我想再度看到哪些作品?』而這這適用於那些我收藏已有相當時日的作品,例如我在30年前買入的1990年代湯瑪斯.魯夫(Thomas Ruff)與沃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作品,也同時包括我剛剛收購的作品,如麥克.塞爾斯托弗(Michael Sailstorfer)或艾力克賈.柯維德(Alicja Kwade)等,我不斷地購買作品,策畫展出就像是我正進行的一場場時代觀點組合的美妙實驗。」

右.挪威暨德國籍藝術家霍倫(Yngve Holen)的超現實雕塑
沃夫岡.提爾曼斯、奧拉佛.艾里亞森(Olafur Eliasson)與伊莉莎白.佩頓(Elizabeth Peyton)是柏羅斯最鍾愛的創作者,他自1990年代開始收藏沃夫岡.提爾曼斯的影像作品,至今已有超過50件的規模,他對此表示:「提爾曼斯對我影響很大。不論是對於生活中許多觀點的啟發,或是我個人對於美的思考方式,他的作品讓我接受了『日常生活常態的美感』。我仍然記得1992年自己在科隆藝術博覽會上第一次看到提爾曼斯作品時的印象,在我眼前的這些作品激起了相互衝突的情緒:無可否認,它們都非常好,但當時我還未曾想過這也能稱得上是藝術。我與朋友曾經針對這個話題進行無數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提爾曼斯的影像作品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讓我意識到、並且接受『日常生活審美化』作為當代藝術核心特質的現實。當20年後我回頭檢視這些照片時,我仍為畫面所傳達的現代感而感到驚訝。它們是如此現代、與我們一起活在當下的時空,我從來不曾想到懷舊、絕對不會想到90年代。」與克里斯欽共享這場藝術收藏美好碩果的凱倫,曾是畫廊經理人,克里斯欽最早入手的一件雷北格(Tobias Rehberger)作品,便是出自凱倫的力薦。

美國藝術家艾弗利.辛格模仿數位化渲染的大型壓克力顏料灰階作品
柏羅斯擁有的五層樓高碉堡,名為「弗里德里希皇家鐵路碉堡」(Friedrichstrasse Imperial Railway Bunker),它的身世與它為了保護公民而存在的身世,同樣引人著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碉堡曾短期作為監獄使用,隨後轉為一座紡織品倉庫,由於其內部恆溫之故,後來則用於存放自古巴進口的熱帶水果,一時有了「香蕉地堡」的綽號。在兩德統一後,碉堡被企業家沃納爾.沃勒特(Werner Vollert)接管,開設為縱馳聲色的夜店。最終柏羅斯於2003年收購了碉堡,並委由德國建築師延斯.卡斯帕(Jens Casper)與柏林建築事務所的佩脫拉.彼得森(Petra Petersson)和安德魯.史崔克藍(Andrew Strickland)合作,將其規畫改造為3000平方公尺的展覽空間,而柏羅斯伉儷位居碉堡頂樓的居所,則可欣賞城市的全景。改造後的碉堡,將原先的120個隔間變成了80個更大的展場空間,厚達兩公尺的牆壁隔絕了所有的外部聲音與手提電話信號,身入其中,你將即時感受到一種孤立感,隨著參觀動線深入內部空間,藝術成為唯一的參照點。

愛沙尼亞藝術家卡亞.諾維茨寇瓦2014年作品〈激活模式〉
★本文為文章節錄,更多精彩內容,請見2018年7月號130期《藝術收藏+設計 Art Collection + Design》雜誌